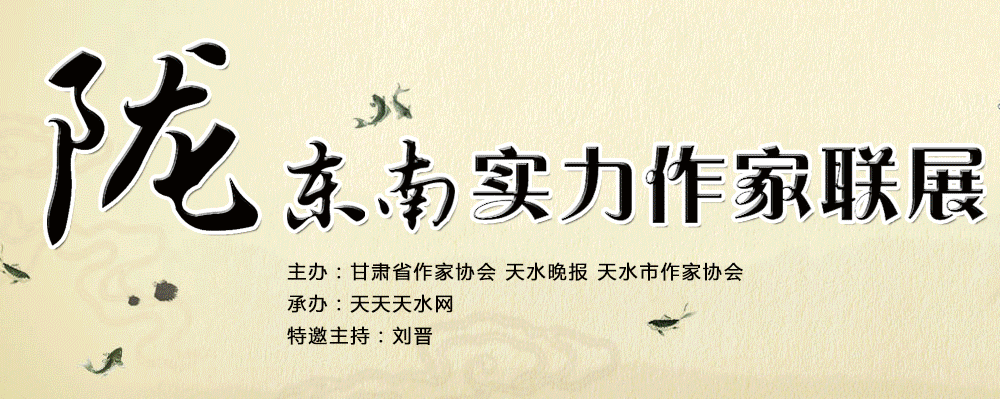
【作者简介】
杨永康,1963年生,毕业于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二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曾获甘肃省黄河文学奖、甘肃省敦煌文艺奖、第三届冰心散文奖、第二届在场主义散文奖、第二届林语堂散文奖,首届三毛散文奖,飞天杂志十年优秀作品奖等。任《黄河文学》中国当代知名散文家新作展栏目特邀主持。

露在外面许多年
□杨永康(庆阳)
许多年都露在外面,故乡的外面,童年的外面。一开始是三五个人,有时候是一大群,弯着腰,手里拿着镰刀。随风缓缓移动,随云缓缓移动,随羊群缓缓移动。很多情况下我们看不见那种移动,只能看见空旷。
空旷的春天,空旷的故乡。一个上午未必能碰到一个影子。有时候会碰到一只惊慌的兔子,一晃就不见了,一转眼就消失了。稍稍定定神,就会看见遍地的青草,满目的青草,童年的青草。就会看到露在青草外面、露在童年外面、露在故乡外面的屁股。稍稍前行几步,会看见更多的屁股。很多情况下屁股们都在随风缓缓移动,随云缓缓移动,随羊群缓缓移动。停下来便怒目相向。怒目相向的时候,那些露在外面的屁股,会骤然使风、使云、使羊群的表情变得僵硬,手中的镰刀会攥得很紧很紧。并不率性地扔出去,只是紧紧地攥着。僵持一段时间才能感到手被骤然的僵持、骤然的怒目相向撕裂开来。从不会感到疼。
有时候会是另一番景象,一个露在外面的屁股会突然愤怒地扔出自己手中的镰刀,另一个也毫不示弱地扔出自己手中的镰刀。有两把镰刀在头顶飞舞,就会有更多的镰刀在头顶飞舞。奇怪的是最终没有一把镰刀扎在那些露在青草外面、露在童年外面、露在故乡外面的屁股上。有一把最狠的镰刀,绕头三匝,扎在一棵树上。许多年后你会惊奇的发现没有疤痕。因为压根就没有谁真正受伤,包括树,包括童年,包括风,包括云,包括羊群,包括那些露在青草外面、露在童年外面、露在故乡外面的屁股。
夏天的时候会有更多的屁股露在外面。一场暴雨过后,雨水四溢。河满了,渠满了,坑坑洼洼都满了。那些躲在彩虹下、屋檐下,被雨水淋湿、被雨水阻隔的屁股,早等得不耐烦了。从彩虹下迫不及待地冲出来,从屋檐下迫不及待地冲出来,从雨水里迫不及待地冲出来,扑通扑通跳进了小河里,跳进了沟渠里,跳进了雨水四溢的坑坑洼洼里。一个猛子扎下去,只有屁股露在外面。满河的屁股,满渠的屁股,满洼的屁股。既便父母找来了,只能看到满河的屁股、满渠的屁股、满洼的屁股。任凭你叫狗儿也好,叫兔儿也好,叫猫儿也好,叫猪儿也好,那些屁股们就是一声不吭,就是不理不睬。漂亮的姐姐来了也一样。
你要扔掉水边那些鞋子,你扔就是了,没有一个屁股会理睬你。你要抱走那些水边的衣服,你尽管抱走好了,没有一个屁股会吭一声的。没有鞋子,可以光着脚丫子回去,扎破了脚,反正心疼的不是那些露在外面的屁股,而是父亲与母亲。没有衣服就光着屁股回去,害羞的不是那些露在外面的屁股,而是漂亮的姐姐。被父母扔掉的鞋子,最终还是被父母拣了回来。被姐姐抱走的衣服最终还是被姐姐抱了回来。整个夏天你都可以看到那些露在外面的屁股。水面静下来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两头来此悠闲喝水的牛。那牛正欲把头伸进水里,猛地瞥见满河的屁股、满渠的屁股、满洼的屁股,惊得闭了眼睛扭头就走,一觉醒来,一睁眼还是满眼屁股。有一只鸟胆子挺大,从一个光滑的屁股跳到另一个光滑的屁股上,实在累得跳不过来,就索性栖息在最迷人的一个屁股上。粗心的人,从远处只能看到一只一动不动的鸟。
秋天的时候,大部分的虫子会安静下来,大部分的屁股也会安静下来。最安静的是秋夜,月儿一点点地升起来,露水一点点进入梦乡,只听得一声吆喝,月光下,会“呼啦”出现一大群屁股,个个手里都操着明晃晃的家伙。然后就是一片嘈杂声。一只偷食玉米的野物,被追得上气不接下气,栽了一个跟头又一个跟头。实在跑不动了,就冲进一座破庙里。庙里的香火早就断了,黑咕隆冬一片。那些凶神恶煞不是缺胳膊就是少腿的,谅那些穷追不舍的屁股不敢进来。
可以安心地睡一觉了。说睡就睡。那野物睡得正香,只觉得眼前一片光亮,偷偷睁眼一看,周围全是火把。心中先是一惊,很快又定下神来。在劫难逃就在劫难逃,反正是个死,索性再睡他一觉。睡就伸开胳膊腿来睡,伸开胳膊伸开腿那才叫睡。要睡就香香地睡,要香香地睡就打呼噜,打呼噜那才叫睡得香。一觉好睡,天亮啦。睡醒啦,屁股们!动手吧!奇怪,怎么没有动静了?得使劲地喊,动手吧动手吧!不对呀。莫非那些屁股们改变主意了?不会,不会,谁不知道俺的肉香啊。香就香。吃就吃。还是不见动静。莫非那些屁股们真动了恻隐之心?不会,不会。那野物正想胡思乱想呢,那些屁股们围过来了。总算围过来了,野物长出了一口气。一个屁股在野物身边不怀好意地蹲了下来,手中捧着一碗水,一直送到野物的嘴边。送来俺就喝,不喝白不喝,喝了也白喝。哈,精神多了。水还真是个好东西。该动手了吧屁股们?俺对得起你们,俺问心无愧了。遗憾的是又节外生枝了,一个膀大腰圆的家伙,抱来一大堆玉米棒子,先递过来一个,吃完了,又递过来一个。这家伙心肠不坏。不过也难说,说不定想撑死俺呢。撑死就撑死,总比饿死强。那堆玉米硬是让俺吃了个一干二净。想使劲打个饱嗝,给那些屁股们看看,没有打出来。没有打出来就没有打出来吧,打出来又能怎么样呢?不行,还是打出来好。要打就打漂亮点。要打漂亮就得站起来。说站就站,刚一站起来,那些屁股们就一阵欢呼。有什么好欢呼的。要欢呼都欢呼。野物刚一欢呼,饱嗝就打出来了。只是不够响亮。得打几个像模像样的。后面一个比一个响亮。每打一个,那些屁股们喝彩一声。还想打,一个家伙过来轻轻地拍了一下俺的屁股说,该上路啦。上路就上路,不就是个死嘛,五百年后还是一条好汉。露在庙门外面的一个屁股见野物半信半疑,轻轻拍了一下野物的屁股说:回家吧!那野物这才屁股一扭一溜烟跑了。
转瞬之间冬天来到了,转瞬之间好多东西看不见了。庙门看不见了。露在庙门外面,露在青草外面,露在水面的屁股也看不见了。可以看见越来越密的雪,越来越矮的谷垛。天一放晴,可以看见一个大大的箩筐、一块撒满麦粒、撒满谷粒的小小空地,与一只在谷垛、麦粒、谷粒间穿行的灰鸽。穿行了很久,便对箩筐、空地、麦粒与谷粒放松了警惕。不吃白不吃。吃。只是转瞬之间又飞走了。几个狡黠的屁股与一截绳子露在空地外面、露在箩筐外面、露在雪线外面,不飞走由不得你。露在外面的狡黠屁股们,自然是一阵沮丧。还好,又飞来一群饥不择食的麻雀。麻雀好对付,狡黠屁股们,一阵狂喜。不巧的是出现了一只小狗。麻雀们又一个不剩地飞走了。狡黠屁股们只好空空地咂咂嘴巴,空空地咽咽唾沫了。
老咂嘴巴、老咽唾沫没啥意思。有一个屁股弄来几个土豆,往火里一埋,一会儿就香气扑鼻了。灰鸽的肉有啥好吃的,听说是酸的。怎么会是酸的?俺父亲的父亲、父亲的父亲,吃过的,一吃准酸死你。那俺就吃麻雀肉好了。听说麻雀肉吃不得的。怎么吃不得?吃了会得一种病的。瞎说。不是瞎说。俺父亲的父亲、父亲的父亲就得过这种病的。病就病,俺就是想吃。另一个狡黠屁股说,到底会得啥病呀?没有见过世面了不是,就是身体发痒呗。发痒有啥好怕的?要是发发痒也就罢了,先是发痒,接着是发烧,发烧过后是昏迷。昏迷过后呢?据说昏迷过后就与麻雀没什么两样了。怎么说?就是羽毛翅膀都有了呗。有那东西好。好什么好?不能飞。为啥不能飞?不能飞才叫病,能飞就不叫病了。哈,说的也是。说话间又一只灰鸽飞回来了。箩筐看不见了,绳子看不见了。雪又飘了起来,越飘越密。又一颗土豆熟了。

▲点击图片进入《天水晚报》陇东南实力作家联展
下一篇独化(平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