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怀念雷达 |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怀念雷达 |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出生于甘肃天水新阳镇的当代作家、文学批评家雷达,是贯穿新时期文学40年的当代重要批评家,新时期文学的见证者、参与者。他曾为陈忠实、莫言、王蒙、铁凝、张贤亮、贾平凹、路遥、刘恒、刘震云、张炜等作家的成长不停地鼓与呼,甘当人梯和使者。他,是当代文坛不倦的“观潮者”。
回望,五年前的仲春,雷达离我们远去。
又到仲春,让我们透过中国作家网刊载的省内外文学名家对他的追忆,来怀念这位文学精神的守护者。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编者

雷达(1943年—2018年3月31日),原名雷达学,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主任、研究员。曾任中国小说学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多届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委。兼任兰州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1943年,雷达出生于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新阳镇。1965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优秀理论评论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优秀作家贡献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中国当代文学优秀科研奖、上海文学奖、中华文学选刊奖等奖项。出版《民族灵魂的重铸》《重建文学的审美精神》(上下卷)《蜕变与新潮》《思潮与文体——20世纪末小说观察》《当前文学症候分析》《重新发现文学》等论文集15部;出版《雷达散文》《缩略时代》《皋兰夜语》等散文集多部。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通史》《中国新文学大系·长篇小说卷》《现代中国文学精品文库》《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近三十年中国文学思潮》《新中国文学精品文库》等。《重读云南》入选上海市高中语文教材,《现当代小说鉴赏》入选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教教科书(必修)。
2018年3月31日,雷达去世,享年75岁。

兰州大学文学院师生| 雷达先生永远是兰大人的骄傲
2018年3月31日,杰出的校友、敬爱的长者、优秀的导师雷达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一生热爱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事业。清明时节,细雨霏霏。春草渐长,怀念悠悠。值此雷达先生逝世五周年之际,兰州大学文学院师生深切缅怀雷达先生。
雷达先生1943年生于甘肃天水,1965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历任《中国摄影》、新华通讯社编辑,《文艺报》编辑组长,《中国作家》副主编,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研究员。著有批评文集《小说艺术探胜》《蜕变与新潮》《文学的青春》《民族灵魂的重铸》《传统的创化》《文学活着》《思潮与文体》等七部,散文集《缩略时代》《雷达散文》《黄河远上》等。雷达先生独立主编或共同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通史》《现代中国文学精品文库》《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等。多部论著和论文《灵性激活历史》《为什么需要和需要什么》《思潮与文体》等获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中国当代文学优秀科研奖,《上海文学》《北京文学》《钟山》《作家》《昆仑》文学奖,《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
雷达先生是新时期最具有原创性和影响力的文学评论家,为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新写实”“朴素现实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冲击波”“新世纪文学”“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文学活着”“灵性激活历史”“传统的创化”等学术话语都是雷达先生的理论首创,至今仍然影响新时代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
雷达先生是新时期文学发展的见证者,被称为探测当代文学潮汐的灵敏“雷达”,其文学批评影响了许多作家与批评家。雷达先生是当代知名的散文家,他散文字里行间充满着诗歌的激情和评论的睿思,闪动着文学批评家思辨的智慧。读雷先生的散文,其性情、神气、风骨、哲思跃然纸上,沛然有雷霆之声。《听秦腔》《洮河纪事》《梦回祁连》《还乡》《黄河远上》等作品流淌着深厚的西部人文情怀。
作为兰大人,雷达先生对母校一往情深。雷达的散文《兰大,我亲爱的母校》表达对兰大的殷殷深情。雷达在兰大百年校庆时寄语母校:“多少年来,我隐隐觉得,有一种叫兰大精神的东西存在过,它支撑和鼓舞着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前行。它是什么呢,它是:踏实,顽强,不怕苦,不服输;是刻苦,坚毅,不气馁,不自卑;是科学,求实,默默耕耘,不慕虚荣;是处贫寒之境而不忘发愤图强,居边缘之地而不坠报国之志。”雷达先生是兰大中文人的骄傲,他的母校情怀是我们兰大人宝贵的精神财富。雷达先生是一位优秀的博士生导师。雷达先生生前一直关怀和支持兰州大学的发展。2002年至2013年担任兰州大学萃英讲席教授,在兰州大学文学院任博士生导师,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学术传承和长远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文学研究人才。雷达先生多次在母校作学术讲座,将他对当代文坛的最新发现、最新思考分享给兰大的广大青年学子。雷达先生等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通史》提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观”问题,被认为是第一部打通中国现当代的文学史著作,至今依然是兰大文学院本科生与研究生的重要参考书。《民族灵魂的重铸》《思潮与文体》等批评著作是广大读者了解中国当代文学思潮的重要文本。望“黄河远上”,听“皋兰夜语”,探“思潮文体”,铸“民族灵魂”。
思寄雷达先生为人为学之风,感怀雷达先生为友为师之德,兰州大学文学院师生永远缅怀杰出校友雷达先生。雷达先生永远是陇原儿女的骄傲,雷达先生永远是兰大人的骄傲,雷达先生将永远活在兰大中文人的心中。
2023年4月3日
白烨:雷达逝世五周年有感
雷达离世五年,但我觉着他并没有远去,他还在我们中间,与我们一起研讨作品,共话批评,打趣说笑。渾厚又宏亮的甘普话语总在耳畔回想,黝黑中含带沉雄的脸庞总在眼前闪现。 但雷达逝去带来的空缺感,也让人感觉愈加明显。我在雷达逝世当晚撰写的一篇文章,结尾时发出这样的感叹:从此文坛无“雷达",文有疑难可问谁?五年了。这种损失与如许空白,依然无从填补。雷达,确实谁也替代不了。 因此,独一无二的雷达,种种回忆更令人无比痛惜,种种往事更令人长久怀念!
2023年4月1日
(白烨,文学评论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 。)
徐兆寿:雷达先生逝世五周年感怀:雷达式遗产的渐显
清明时分又至,给亲人上坟时,自然便想到雷达老师。他对我,如同亲人一样。但令人惊悚的是,他居然离我们有五年之久。这么快!
先生离世的这五年,也是我们离开他的教导和帮助而独立打拼的五年。每每在一些评论场合,我便自然会想到先生。我在想,如果他在,他如何看待现在的文坛现状,如何评判一本小说和一个作家,是一味地捧,还是不由分说剑走偏锋地将其打倒?我发现,他往往是中庸之道。无论是任何一个作家,他都要指出其优点,同时又指出其缺点。即使是已经成名的大作家,他也会指出其弊端。但是,他又爱护着每一位作家,绝不一棒子将其打死,而是将其扶持。此中宽容、情怀与中庸之道,非一般人所能拥有。此外,他的评论少有长篇大论的,即使引用理论也是恰当而止,绝不像今天的很多长篇大论那样,使人不能卒读。他一直强调,评论文章也是要讲“理性的激情”,使感性与理性相结合,要使评论文章也成为美文,而不是死文。我想,这可能是他留给文坛的“雷达式遗产”,是我们应当学习和继承的。
清明已至,写这些文字,在心头为先生上一柱心香,愿他天堂快乐!
2023年4月3日
(徐兆寿,复旦大学文学博士。现任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甘肃省文联副主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甘肃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甘肃省电影家协会主席。《当代文艺评论》主编。)
李晓东:如果雷达先生还在
又到清明时,京城春来,天水玉兰花开,雷达老师却已离开我们四年了。一千多日日夜夜,物是人非,但中国文学界没有忘记他。多少文学研讨会上,发言时,一句常说的话,“如果雷达看这部作品……”雷达,已成为中国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化身与难以逾越的代表。他带着天水口音的、亲切缓慢的话语,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中国文坛的“正音”。一个研讨会,雷达来了,质量就有了保证,就能发现作品的优长以及今后改进的重点。他研讨、评论的作品,贯彻了整个新时期中国文学,尤其是小说。每一部,他都认真阅读、仔细笔记,写出讲稿。斯人虽已逝,每念及他的作风,仍令人怀念而感动。我曾组织中国作家走进王家庄雷达故里,在阳光饭店召开雷达思想研讨会,参加天水师院雷达文学馆开馆和纪念研讨活动。每一次,都深为感动、大有收获。天水作为中华文化源头区,不仅伏羲一画开天、文明肇启,更文脉传承,代有所胜,期待天水文化文学如天河注水般神思滔滔、再塑辉煌。
(李晓东,文学评论家,中国作协社会联络部主任。)


高凯:想念雷达
又是清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写过一篇关于雷达的人物通讯《检测文坛的雷达》,开篇第一句话是“雷达是一位能让人长久凝视的人”。今天看来也很贴切。不过,今天不得不把“凝视”改成“想念”了。
一个被自己长久凝视的人突然逝去,不免让人悲伤和惊愕不已。所以,雷达溘然离去之后,我除第一时间代表单位赴京参加吊唁活动之外,还与爱人靳莉紧锣密鼓编选了雷达的纪念文集《挥别大师》,并在第50天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当初,之所以编这本书,就是为了记住雷达,而记住了他自然就会经常想念他。记得,敲定“挥别大师”四个字作书名并请贾平凹题写时,我问雷达应该是一个大师吧,平凹毫不迟疑地说:那当然! 大师雷达无可置疑。雷达的牛,以及雷达的好,已经有不少人用文字表达,这里我不想再赘述,我只想简单说一下我想念雷达的原因:我们都因为文学活着!
检测文学的雷达永生永世!
2023年清明时节于北海
(高凯,作家,甘肃省作协副主席。)
弋舟:雷达先生若还在,他会怎样看?
雷达先生辞世五年了,这五年来,每遇令自己困惑的文学现象,我都不禁会想:雷达先生若还在,他会怎样看?于是,我才恍然意识到,原来,“雷达怎样看”,在我这里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内在的尺度,用以丈量人心的远近、文学的高低。
(弋舟,作家,陕西省作协副主席,《延河》副主编。)
秦岭:先生在这边,也在那边
如若不是感应,京津地区何来这哽哽咽咽的清明碎雨?料想老家天水那边,也如宣纸上的水墨云烟吧。
这是雷达先生谢世后的第五个清明。2018年3月31日,先生挥手告别了人间和人间的我们。我辈这思念、这心结、这怀恋岂止于传统节气的雨滴?岂止于对先生丰硕成果的回望?岂止于对先生耳提面命的追忆?2001年,《天水日报》的赵晓霞女士委托我采访先生,我在赵本山影视团队首席编剧张继兄的引荐下,完成了对先生的初访,于是,我的另一种时光在文学与乡情的山鸣谷应中开始了。斗在转,星在移,可始终未曾转移的,是岁月里的聆听、感悟和自我反思。2009年,先生在《光明日报》著文《在<皇粮钟>里找到中国农民》,为我寻找文学的中国农民鼓了劲提了气。后来的俗世中,我始终未停下寻找中国农民真实模样的步履,可如今要找到先生确是万难了。清明一年一度,让所有在着和不在的人在纪念和被纪念中有了可能的对视,可我还能说什么呢?先生根在天水,可我等凡夫俗子几经呼吁,仍未能完成对先生新阳镇旧居的复原和修缮。抱憾和失责、汗颜和纠结,让我今天的纪念显得缺斤少两,没个落点。
纵然不甘,这清明的雨终是下了。感觉先生在这边,也在那边。他只是打伞出门,顺手关机了。
不由给先生发了微信:“先生,这五年,那边的一切,都好吗?”
2023年4月于天津观海庐
(秦岭,天水籍天津作家,在海内外出版各类文学作品20多部。)
毛晓春:慈颜长存,音容犹在——写于雷达老师五周年祭
雷达老师去世已经五周年了,正如王若冰老师所说,回忆雷达就是把心里那伤口的疤痕一次次揭开。是很疼很痛苦的。但是他那西北汉子粗狂的面容,黄钟大吕般的声音一直还在耳边回响。常常,我在夜深人静时翻检和他在一起各个时期的照片,细细在静夜中品读他的文章,看他在北大百年讲堂上为我新书首发仗义执言的视频。他不单是文学上我的老师,是我走向文学之路的引路人,我心里得一盏不灭的明灯。在生活中,他就是一位长辈,一位父亲般从做人做事严格要求我的长辈。
一个人虽然走了,但能使人永远记住他的点点滴滴,永远让人回忆他的一切是很难得的。雷达老师活着时,我心里有种十足的踏实感,每当在文学上困惑,在生活上迷茫时,找他聊聊,会使人很释然,这几年他不在了,老觉得心底一种空荡荡的失落。在故乡老家人的心里,也是每每的遗憾,每当提起雷达老师,都是不无遗憾的说:“咋就这么快走了呢?”
雷达老师的离去,在我的心里失去了一盏明灯,失去了一位文学上的导师,失去了一位好父亲般的长辈。在文学评论界这种空缺感是一种断层,对小说家而言失去了一位评论大家。对家乡失去了永远的游子。
2023年4月1日
(毛晓春,笔名雨枫,甘肃天水人,学者、作家,金石书法家。中国文联主管《神州》杂志社副社长。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金错书研究中心主任。)


刚杰•索木东:文学的相约
转眼间,雷达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五年了。想起先生的时候,总会想到他的爽朗,他的博学,他的平易近人——最初应该是通过徐兆寿先生和张晓琴女士伉俪认识雷达先生的。有一年,他们相约去看那时候还没开发成旅游网红地点的扎尕那,因为我是甘南人,想邀我同行。因为个人工作太忙的缘故,当时我未能成行,他们就和唐翰存兄一起开了一台车去了。后来,先生写下了长文《天上的扎尕那》,他的本意,还是希望能保留那里的天然淳朴和自然纯粹。当然,后来扎尕那火了,成了甘南迭部的旅游胜地。
后来,在很多文学活动中,会偶尔遇到先生。他远远看到你,就会叫你的名字,然后拉到跟前问候,甚至会介绍给身边的人,让我们这些文学爱好者和晚辈后学倍感温暖和亲切。
先生仙逝后,大家都用很多形式悼念他,我当时也写了一首小诗。有时候,翻阅结集出版的《挥别大师——当代中国文学视野中的雷达》,看那么多人写下来的回忆文章,就能看到先生高大温暖的背影,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旷野上伫立成一座丰碑。 2023年春天,协助甘南州文联编辑一本文化名家看甘南的文集,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先生的《天上的扎尕那》。通过兆寿兄取得了先生亲属的同意,再次拜读这个名篇时,先生的音容笑貌和人格学养就又浮现在眼前了。
先生其实并没有真正离我们而去!每个丁香花开的季节,他和他的文字,在辽远空阔的北方大地上,又将迎来一个生机勃勃的春天。
刚杰•索木东敬书于流珠斋
(刚杰•索木东,70后藏族诗人,甘肃卓尼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诗集《故乡是甘南》,现供职于西北师大。)
赵武明:身高为范,德高为师
五年易逝,五年感怀。想起和先生的交往,点点滴滴,受益匪浅。在文学界来说,“雷达”一直是勇猛而不老的标志。在长达40年的文学批评工作中,他始终保持着敏锐而精准的判断力,活跃在文学现场,以灵敏的触角见证着当代文学的发展。只要有先生的评论或力作,我总是会好好学习。他的作品凝练厚重,他的学识敦厚深渊。先生留给我们学习的不仅仅是作品,更重的是人品。先生甘肃文学界的福星,是甘肃创作者的福音,是他撑起甘肃文学的大厦!
清明临至,泪雨纷纷,肝肠寸断。天籁之声,流水潺潺,掩面婆娑。五年很长,五年很短。草木默哀,今天的兰州雨雪纷飞,那是为先生哀悼!嘘!先生休息了!他需要静静,因为真的太累了,永远看不完的书也该放放了,永远写不完的字也该停停了!这个春日,他歇息了!
皋兰山巅风呜咽,费家营里寄哀思。安息吧,先生!
斯人已去,空留悲恸。滨河路上花盛开,人间四月芳菲悲。
长歌当哭,痛定思痛。万千思绪,此刻失语。
黄河远去,先生永存!梦回祁连,且听新阳镇上声戚戚。
雷达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赵武明,文化学者、作家、编剧、纪录片策划撰稿人,资深媒体人。甘肃省网络作协副主席。)
雷希文:深情难忘雷达叔叔
时光如水叔叔已离去五年了,他在我们大家心中一直记着的,他待人很实在亲切,他从小和我们在一起玩,每从兰州来老家要住一段时日和我们都玩的开心,记得叔叔兰大毕业的一年来天水市和我们见面,他总是很开心,并一起去文化馆看了全市美展。正好看到了我的两幅画,他对我说,将来一定耍争取一等奖。对我鼓励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二零零五年左右他来天水我单位看我,就我绘画创作事宜谈了近两小时,这次对我邀励是很大的。
此后每来天水他都打电话给我。二0一五年他和夫人来天水时他支气管发炎犯病,返回时我和姐姐送到车站站台上,没有想到他也是最后一次来家乡的,也是我们最后的见面。叔叔的教导我永远铭记在心,他的业绩更是我们家乡人的骄傲,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雷希文,生于甘肃天水,1949年生。麦积山艺术研究会理事,天水美协副秘书长。)
尔雅:纪念雷达先生
我很怀念雷达先生。他是一个热情率真的人。多年之前,我加入中国作协时,雷达先生极力推荐,不吝溢美之词。后来去鲁院学习,雷先生也是热情地向有关方面推荐。实际上,我们之间的私人交流很少,大部分相聚,都是在会议上和其他的群体活动里。后来雷先生生病,有两次我到了他家里附近,但雷先生不愿意让我们看见他生病的样子,终究没有见到。想起来觉得很遗憾。有时候我觉得辜负了雷先生的期望。但雷先生对于后辈的赞美从来是出于公心,出于他广阔的胸襟、出于对文学的热爱和赞颂。他是一个好人。在日常生活中,我不善于表达自我的情绪,也不会轻易地评价文学界的同行。但我觉得,雷先生是一个值得感谢和怀念的人。
(尔雅,作家、学者,现居兰州。)
向春:你怎么选择这么美好的一个春天离开
梨花开得那么急
接着是桃花鲜艳得
没心没肺不谙世事
冬天都熬过来了
你是想让儿孙和朋友们送你时
不太冷吗
你怎么舍得在春暖花开的时候
离开
雷容带着孙儿正在回家的路上呢
老伴儿出去买菜
拎回一蓝子
色香味俱全的天伦之乐
老伴儿说马兰头可嫩了
冷了的是血肉
电脑里的文字还没有冷
一个个一行行恰如你
风骨棱棱
雷容啊摸摸爸爸的骨头
如果还热着,
那是他不想走
他己经顺应了这个世界
而红尘却辜负了他的天真
就想简单地活着
看一眼蓝天听一声鸟叫
就不行吗
天水的浆水熟了
早春的麦积是新的
新长出来的一捆麦子
没有了雷达的天水
没有了雷达的麦积
没有了雷达的浆水
还有什么意思
唉
(向春,原名任向春,作家。曾获第16届《小说月报》百花奖、甘肃省敦煌文艺奖等奖、黄河文学奖、《作品》金小说奖等。现居兰州。)


张继红:怀念吾师
雷达老师的博士生们曾有一个“雷门雅集”微信朋友圈,大概是在微信刚刚兴起时建的。雷门雅集,集虽不算雅,但甚为热闹,刚刚学会“微信”的雷老师也被邀请入群。走出兰大后,师生彼此见面少,但在群里共享“雷达观潮”的海阔天空和别后“团圆”的短暂时光,也是难得的聚会。那时,雷老师仍然宛如当代文学星空下的扎尕那,冷峻、激情,不无神秘,又充满人间烟火,令人向往。雷老师走了,我们“在流连与惊惧交织中,扎尕那在我们的身后越来越远。我们仿佛从天上一步步降到人间。”雷老师走了,他说:“我应该在这原始古老的国度里做一只自由的鹰。”“雷门雅集”也因此不再热闹。为纪念雷老师,我们建了新群——“送老师一程”。五年时光,逝者声远,音容宛在,但我们总会情不自禁地溜到“雷门雅集”,时光倒流般回到过去——雷老师还在、群里谈笑风生的日子。无论触景生情,还是因文及人,每每会有一个词语或一个场景,与观潮者雷达有关,与当代文学有关。怀念雷达老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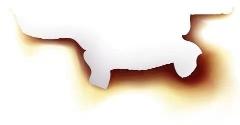
新阳镇(节选)
雷达
或许,从出生那一刻起,我就注定了与天水、兰州两地无法分割。我的母亲祖上是临夏人,实为兰州人,父亲却是天水人。我本人生于天水,一岁大点被父母带回兰州;从那时起直到1965年,一直在兰州,却不时往返于兰州和天水两地。
在外人看来,天水和兰州不都在甘肃吗,能有多大区别呢。其实,他们哪里知道,甘肃这块地方很怪,幅员辽阔,民族杂多,地貌错综,文化斑斓,是个至今也没有得到真正广泛认可的神秘的文化大省。它在地图上呈长条状,有人说像一只哑铃,有人说像一只马靴,有人说像一条飞龙,它广大到41万平方公里。从兰州坐飞机到北京的距离,与在本省从兰州飞到敦煌的距离竟相差无几;至于各处文化的错杂更是难以尽述。所以,天水与兰州两地,文化的异质并不奇怪,就口音、习俗、历史、风气、艺术、性格倾向、精神气质而言,都有莫大的差别。我从小穿行于两种文化之中。天水给了我一个广大的精神空间。
我的家乡新阳镇就很值得一说。它距天水县城约六十华里,是渭河上游的几大古镇、名镇之一。我小时候它叫“沿河城”,却并不见城墙,不知何以以城名之,现在的人早不知“沿河城”为何物了。南面壁立着凤凰山,似屏障,颇雄奇,也叫邽山,据说古时属上邽县管辖。我发现,天水农村的风俗情调与《白鹿原》或高建群《大平原》里的关中农村极为相近。原来,一切皆缘于一条伟大的河流—渭河。渭河发源于甘肃渭源的鸟鼠山,向东流过甘肃东部,到陕西的宝鸡出大散关,历经无数岁月形成了八百里秦川,最后在潼关入了黄河,全长近900公里,乃黄河最大的支流。记得钱穆先生曾说,所谓农耕文明往往诞生于河谷地带或冲积平原。细审之,渭河流域农耕文化成熟之早,其发达绚烂程度,应在黄河与长江文化之上。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大地湾文化,半坡文化,何能离得开浩浩渭水呢。
渭河从甘谷西端流进了新阳镇。它从胡家湾和裴家峡的中间冲出来,绕过四嘴山脚,拧一道大弯,硬是冲积出一片肥沃的河谷盆地新阳川;河水从谷地中间穿过,呈肘弯型,将镇子劈为西南和东北两半。再往东去,便是有名的卦台山了,伏羲画八卦的地方,属三阳川境,是又一处名镇。我出生那年,“五四”运动健将,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曾登上卦台山,发出过“智缘书契始,一画破鸿蒙”的赞叹。
与黄河的雄浑不同,渭河大多数时候显得比较温婉,连水鸟也眷顾这片美丽的地方。我小时,从冬到春的河滩上,总有灰颈鹤和白鹭鸶优雅安详地散着步,它们有长长的颈和细细的腿。少年的我极爱它们,有时大胆贴近到只几步远,都伸手可及了,它们却神态自若,并不惊飞。新阳川既分为西南与东北两面,集市在南面的温家集,我们居住在北岸王家庄、赵家庄一带的人要赶集,要买卖东西,或上天水县,就非得过渭河不可。秋冬至初春,渭河水瘦,人们就架起草桥,草桥柔软有弹性,独轮车滚过时,忽闪忽闪,发出轻轻的呻吟。一到盛夏,渭河会变脸,露出凶相,发大洪水后巨石躺满河滩,景象很是恐怖。平时虽也有渡船可渡人,但常翻船,淹死人。聪明的村人就想出一法,在河两岸各栽一大木桩,拴上铁环,在钢丝上系一大箩筐,一次可坐四五人,来回拉动,像土造缆车,大大方便了老人妇人和孩子。
在我的记忆里,广袤的河滩地种的全是高粱,每一株都像红脸蛋的女孩或英武的汉子一样,无边无际,血色深浓,随风摩挲出哗啦啦悠远闷暗的声响,好像里面藏着无限的秘密。看电影《红高粱》野合的那片高粱地,心想,比起我老家的,真不算什么。高粱在我家叫“秫秫”,是主食。“秫秫”吃起来酸涩,不好消化,据说因为产量高,乡人一直在种它,吃它。只有过年时,高粱才有点可亲,用高粱酿的“稠酒”好喝,装在一粗而高的瓷罐里,下方凿个嘴儿,形如小孩的“牛牛”,一拔就撒尿似的冒出来。我一觉好玩,二觉好喝,喝起来没完,几次醉倒。我平生喝白酒没醉过,若说醉,也只醉在这稠酒上。
在我看来,我的乡亲们是些最有文化的人。这些平日的泥腿子、庄稼汉,扛长活的,一到大年初一早晨,一个个从门楣上刻着“耕读第”,“诗书传家”,“仁义孝悌”匾额的院子里走出来,大都换上干净的长袍,彬彬有礼,表情肃穆,背着手儿,缓缓地鱼贯登上四嘴山的家庙,去敬香祈福。我在他们脸上看到了对祖先、对传统的无比虔诚和敬畏。有些人的发型很怪,前半部脑壳剃得精光,后半部脑壳却蓄满长发。这是否晚清时代的一种孑遗?康有为,梁启超似乎就留过这种头。我一见就想笑又不敢笑。这种发型,在我印象里,直到大跃进时才不见了。新阳人的方言也独特有趣,把奶奶叫“婆”,把爸爸叫“达达”,把你的叫“牛的”,把我的叫“敖的”,把舅妈叫“妗子”,把最小的叔叔叫“碎爸”,等等。家乡人除了勤于农耕,就是渴望孩子成为读书人,尤重视书法字画;看一个孩子读书好坏,先看毛笔字写得如何。外地公干的人一旦返乡,立刻就会有人手持宣纸登门来求“墨宝”。我毛笔字不行,这成了我多年来怕回老家的潜在原因之一。

还乡(节选)
雷达
细雨中的路面不起尘埃,清风徐来,草木轻摇,天宝来了兴致,扭头说,这天气坐车最舒服了,我报以颔首微笑。其实,他也许永远不会想到,此刻我心中涌起的是一种莫名的失望情绪。我当然知道,世间原本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可人又是一种没有永恒的念想就活不下去的动物,于是在心灵深处贮藏许多美的回忆的吧。你经历的生命的辉煌,你品味过的诗意的瞬间,你热恋或倾慕过的女子,甚至一种吃食、一个物件,在世俗生活的潮流中都会变色变味。美,最怕第二次光顾。那么,是否最好不轻易“启封”?不要重新碰“她”?这岂不又有违人类追求美的天性了吗?
哦,故乡在雨后的雾岗中出现了,她静静地斜倚在河谷里,似在等待我的到来。渭河如弓弦划出一道弧线,好似我臂弯上鼓突的血管。
可是,我的渡船呢,我的因独轮车滚过而呻吟着的草桥呢,我的蓝蒙蒙的布满松柏的坟院呢?我的波光闪闪的水渠呢,我的高低错落的永远哼唱着的磨房呢,还有我的鳞次栉比的乌黑瓦屋顶上软软的、悠闲的炊烟呢,怎么全都找不见了。是我的眼睛迷蒙了吗?我只看见一座曾在电影里见过的钢铁吊桥悬浮于渭河上,又看见昔日低矮的瓦屋群里,像突起的蘑菇似的,伫立着不少两层小楼,让人想起京沪线上的江南农村。不过,待我抬头看见四嘴山上蹲伏的家庙时,才实实在在觉得到家了。家庙油漆一新,灼灼照人,是这里最雄伟的建筑。两年前,老家来信募捐,说要翻修家庙,还说我名列乡贤第二,曾让我哭笑不得,现在“乡贤第二”终于回来了。
汽车下到谷底,沿着渭河跑起来。路边是刚放学的娃娃与赶集的村民。奇怪他们管自走路,对汽车和车中的“乡贤”并无兴趣,不复多年前对汽车的好奇。记得有年我从城里来,一个跑在场院用链枷打麦的小脚老婆婆问我:“都说汽车汽车的,到底是驴拉哩还是人掀(推)哩?”我说,“驴也不拉人也不掀,它自己跑哩。”老婆婆惊诧道,“噢,这么说它是个活的?那它吃啥哩?”我说“吃汽油哩。”老婆婆于是拉长声啧叹了许久。唉,我的故乡曾经是多么贫穷和蒙昧啊。而现在,还有谁稀罕汽车呢。
我低头下望,看见河里拥后簇的浪花在急急赶路,它们像不断伸出的手爪,似要揪扯住我,仰面诉说沉埋河底的往事和无尽的悲欢。我有些悚然了。还是一个突遇的场面,我把拉回到现实来:车进村口时,我瞥见卖凉粉的小滩,那个左手平托一块粉右手用刀快切的老妇,不正是五娘?我差点大喊起来。不料,天宝却淡淡地说:“什么五娘?她要活着,还不快一百岁了?那是她女儿淑贤。”我惊异地回望叫淑贤的女人,那面相,皱纹,装束,真是酷似五娘,且含有一种难以言喻的神秘和苍凉。这一瞬间,我感到了时间的古老,又体味着岁月的无情。
天宝和他的车到别处去了,我独自沿着泥泞、熟悉而又陌生的村路走下去。路上不时遇到一些我好像认识,又不认识的男女。乡人老实,不敢贸然向生人,特别是干部模样的生人打招呼,或者他们也在回忆,于是双方鹄立着,相顾无言。我此时忽然觉得,人一到这里,连走路的速度都放慢了,昨日的拥挤、浮嚣、嘈杂全都远遁,周遭的宁静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隐隐有渭河的涛声传来,偶然有唧喳的春雀儿掠过,让人想到,城里人按钟表的节奏旋动,这里可是依自然的节奏生活,你本身就是自然的一分子,你与蜿蜒的路,高阔的天,含烟的树融为一体了。
我终于跨进了门楣上写着“耕读第”三个大家的家门,字迹的斑驳显示着它的古老。陇东南一带,即使赤贫的农家也不忘在门上漆这三个字,表示对农耕,读书,孝悌的敬重。这个门我不知进出多少回了,此时跨入,顿感生疏;异母兄嫂,侄儿女辈蓦然相见,大有“相对如梦寐”之感。然而,正像很多文章里写过的,欢乐的气氛很快把我包裹。亲房本家一些上年纪的人,也朗声呼喝着我的小名,跺着泥鞋来了。我被推搡到炕上,盘膝而坐,连忙一遍又一遍地抛撒香烟,把糖果点心塞到挂鼻涕柱的碎娃们手里。不知怎么一来,我开始改用略显生硬、毕竟地道的乡音说话。改为乡音即使我腼腆,又使我暗暗得意。这才体味出,觉见上海人的一见面即用上海话叽哩哇啦交谈,那么得意洋洋的原委。过去我以为那是很可憎的。我望着炕沿下一些叫不上名字的碎娃,我的后裔,看他们用黑乎乎的眼珠盯视陌生客的傻憨态,恍惚觉得,他们中间的一个就是我。时间猛然间倒流回去,真不知今夕何夕,身在何处。

1、凡注有“新天水讯”的稿件,均为天水日报社版权稿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或镜像;授权转载必须注明来源为“新天水”,并保留“新天水”电头。
2、凡注明为其它来源的信息,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新天水客户端(网站)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