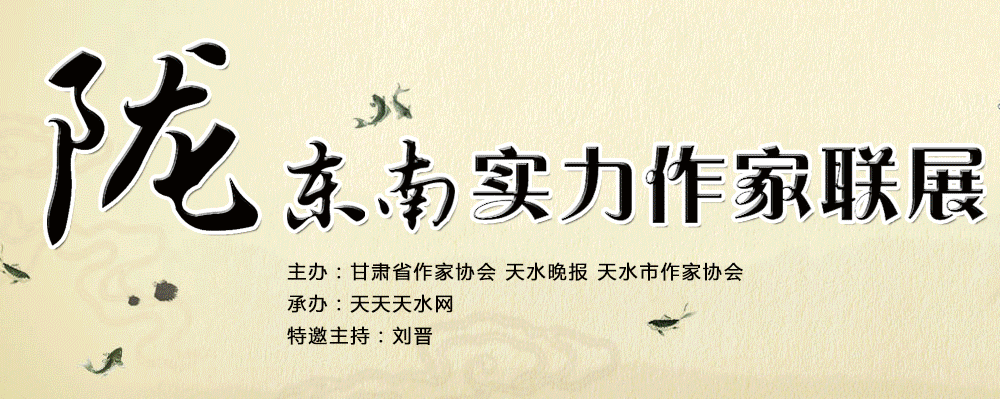
【作者简介】
王晓燕,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甘肃渭源人。小说在《西部》《朔方》《清明》《芳草》《文学界》《飞天》《青年作家》《广州文艺》《山东文学》等刊物发表。曾获黄河文学奖一等奖。现居天水。

浮生梦
□王晓燕(天水)
彩虹爸吸溜一口滚烫茶水的功夫,就把我们那条小街走到了头。这样小的一条街上,依然应有尽有。最让人吃惊的是,还有一家“电影院”。
我们一直住在父母工作单位的大院里。不知谁家的公鸡,会带着一群母鸡抖缩着脖子窥探挪步进来,杨宗祥家的那头光溜溜的粉猪,随便挤过立在大院门口的人腿就进来了,喊都喊不住。彩虹妈种的那块菜地,一般是这头猪一头扎进去的地方。
我们小孩子往外跑。大礼堂是个极其空阔的地方,足有人家的足球场那么大,一直向里走,一幢完全称得上是恢宏的建筑,把正脸儿朝向小街,把隐密沉重的大屁股甩向老君山下。石拱的屋顶下,是个四四方方的舞台,但凡秦剧团来唱戏的时节,舞台上会悬挂起丝绒的帘幕,舞台一下就有了几分贵气和神秘。
我们跑。沿着左侧的小径一直向里冲,拐角的路旁,站了两排白杨树,高而直,要不是这些树,这里,会落寞得很。真正迷人的,是舞台后面那个大屁股,那里即我们的电影院。
我们跑,此后再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让我们有如此的速度和激情。
放映员一位姓王,一位姓张,他们俩人轮换着站在门口卖票。那些年,放映的都是些抗战片,要么就是唱戏的,吱吱扭扭半天唱明白一句。可是呵,我们都看得如痴如醉。不管放什么,我们都会仰着脖子陶醉上两个小时。
事实上更爱看电影的人是我妈,只是琐碎的生活渐渐将她这番的热情摧毁了。电影,是小街上所有孩子的神话。博尔赫斯的图书馆是他的天堂,可我们的“电影院”,即是那样的天堂。进电影院,先是有种神秘的仪式感。在电影开场前的那几秒钟里,我和彩虹都感觉到神灵的闪现,那一刻,我们长了翅膀,由着神灵的牵引。
逢集天,我们的爹妈都忙得要命。在我和彩虹第一次发现白天放映的影片跟平时在晚上放映的完全不重样且都比较精彩之后,我们几乎每个逢集天,就都跑来看了。在最后一节课,为了争取到那宝贵的最先能跑出教室的几分钟,我和彩虹把肠子都想空了。
为了不让父母发现,有意弄出努力用功时间紧迫的局面,将几本书马马虎虎掉落在床边边上,口袋里随手装一点吃的就往外跑。
跑,是我们对电影最好的膜拜方式。为了能看一场完整的电影让我们变得近乎英勇,让我们激情澎湃双目炫亮。想想,两个女孩子,苍黄着两张小脸,奋力挤过集市上的人丛撒腿冲向大礼堂的场景。
彩虹大我七岁。彩虹回家总是先梳好头发,弄整洁衣服,还不忘帮她妈干几把活,我则乱发枯相,我妈她老人家就叫我毛焰兽。我总会在最恰当的时机出现在阿姨面前:让彩虹去我家写作业吧。不识字的彩虹妈眼神里有那么点蒙,但还是催彩虹快去。我妈订了很多电影杂志,彩虹常借过去读,缝缝里的小字她都看了。彩虹妈认为,看什么样的书,都是在学习,何况是我妈看的书,她极为信任。当然我的眼神一定是无比的可怜诚恳。
那天我去喊彩虹时,阿姨不像以往那样热情,我不知道为什么,在电影院里我心里老觉不安。我抬头往上望,看见了大礼堂高高的屋顶,粗壮的房梁,灰尘顺着放映机前投射向荧幕的那道直直的光线飞舞。头一次,我暂时脱离开了意醉神迷的观影者和荧幕,想了一些不知所以的问题。
我恍惚觉得是在一场幻梦中。我看到,那只是座巨大的房子,既没有帘幕,也没有座椅,没有专门的放映室,让人恐怖的是,它竟然没有窗,只有两扇门,原本是一层黄土的地面,已被踩得比砖头还硬实。灰尘在飞荡。如同那天我和彩虹游移不定的眼睛和心跳。墙后面有什么?屋顶会不会突然塌下来?
然而我最担心的,是放映机前的灯光突然亮起来,那意味着,梦境坍塌,我们得从这暗黑里走出去,走到日光底下去。从自由和天堂,走到小街上那闭塞狭隘得让人烦闷的事物当中去。
这诱人的暂时脱离了人世的时光啊。
阿尔·帕西诺!彩虹尖声叫了起来。
你没法晓得,那天上映的影片对两个视电影为神话的少女来说,是怎样一种喜悦。
据说,一位在大城市里上学的青年还乡,不知从哪租到了一部《教父》拿来小街上放。
彩虹放肆的抽泣声在安静的人丛里像一道尖利的光,鲜亮而畅快地四射。
那天下午,我和彩虹迟到了,我们垂头站在高高的台阶上接受全校师生的注目和嘲笑,脖子都快折断了,直到全校师生都走完。
一丘之貉!好好展览一下!我们的老师很会骂人。彩虹认为,这是我们人生当中最不堪忍受的耻辱。为了讨好她,我大谈那个男星,彩虹抬起头来看着我。
我愿意为你忍受一切。彩虹神色恍惚地说。
我看不懂彩虹的眼神。
从那天以后,彩虹妈再没允许彩虹在正午时分到我家里来过。我仿佛也一下子才意识到,我是个女孩子,那样不顾一切地狂奔向大礼堂,是比站着被展览更让人感到羞耻的一件事。
我爸妈也终于发现了我的诡计。后来的逢集天,我妈必要赶在我吃午饭那点时间里,穿着白褂子,背靠着门站着一边看表,一边盯着我心急如焚地吃饭。喏,电影已经开场。喏,这时进去,演了啥已不那么好猜了。喏,我偷瞄了眼我妈。我恼火又不敢说什么。我吃得越来越斯文秀气,我装得矜持了,反正,看不上电影,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沮丧的。
不被允许看电影的日子里,我翻遍了那些电影杂志。我更迷恋约翰·特拉沃尔塔,或者尼古拉斯·凯奇。理由也许就是彩虹迷恋阿尔·帕西诺的那种理由。
小街上的夏天,是突然逝去的。夜里,满床抓摸被子。清早,厚衣衫堆在床头的椅子上。热情之火,捂在身体里,衣服穿得厚了,风就钻不进去。开始还熊熊自燃,慢慢,没了意思。
向着礼堂奔跑的速度,随着那年冬天的到来,缓慢了下来。
西方国家称电视为培养傻子的盒子。在我们那条小街上,大人小孩的闲暇,很快被电视机控制了。他们从没考虑过,它会培养什么。
纳博科夫说,好的艺术,都是神话。
那时,我们不懂什么叫艺术,但我们千真万确曾经体验过,来自于电影的神话。那样一厢情愿的、专一浓烈的、如痴如醉的意乱情迷呵。
小街上。简屋陋巷。季节和人的生死,使人感觉到,人世在变幻,这个世界,也在发生着变化。
那些年,在小街上,那道门是窄小的,却是通往奇迹之门。一件隐秘且没法判断对错的事,当两个人一起去干的时候,似乎就可能减轻负罪或羞耻感。这是不是两个年龄相差很多的女孩子不停奔向对方的真实原因呢。
绕过一道窄小的铁栅栏,两扇木门,总是一扇开启,一扇闭合。事实上,我们从不曾往那道门的旁侧、高处和低处看过一眼。我们最初的梦想,我们一心想着的,是不停地飞一样冲进那道暗黑的门里去。
那道门后面,光影流转出另一个繁烂时世。
不管他叫迈克还是阿尔·帕西诺,本·阿夫莱特还是茱丽耶·罗伯茨,管他叫什么,只有我知晓,对彩虹来讲,都不重要。彩虹为之哭泣,为之神魂颠倒的,也非那个有着意大利血统,目光凌厉的矮个子男人。
在那个图书馆永久性关闭的地方,我们迷恋过的,只是一座没有布景没有座椅甚至没有灯光的空房子。空房子里暗黑的气流,杂乱的呼吸,暗中看不见的支撑站立的双脚,一双双不曾对视过的眼眸,集体迷恋着同一段光阴,同一个人,同一段剧情。你眼前的脑袋,下一秒会莫名其妙转换成另一个。这些人,有明眸,却看不清他们的身形。这一切,太像是一场梦。一场集体做着的浮生梦。

▲点击图片进入《天水晚报》陇东南实力作家联展
上一篇包苞(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