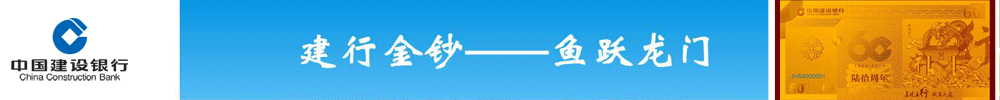 |
探测当代文学潮汐的“雷达”
——访文学评论家雷达

在中国作家协会的十楼会议室,雷达有一个几乎固定的位置,即主席台下面右手的头个座位。多数研讨会步入专家讨论的正题时,雷达总是第一个发言。真诚坦率,又视野开阔,雷达的评论实实在在,不掺一点儿水分。而这不动声色背后,却是他几十年阅读与写作的积累。
近年来,雷达的作品一部接一部:他参与撰写并主编的《近三十年中国文学思潮》以最能体现近30年文学的思想灵魂和精神本质的若干问题作为论述焦点,把复杂的现象和浩瀚的作品糅合到一系列问题的阐述中去,描绘出近三十年来波澜壮阔的中国文学的思潮起伏的画卷;《当前文学症候分析》充分肯定了当前文艺创作的优秀成果,又尖锐地指出了当前文学创作存在的普遍性、倾向性问题,引起了文学界强烈的反响;《重建文学的审美精神》搜索当代文学关键词,聚焦茅盾文学奖,构建作家作品档案,并由此引发许多边缘思绪,是一部颇多创见的论著。
白烨在《批评的风采》中专门有一章写到雷达的小说评论,评价“雷达是名副其实的‘雷达’”。这确实是一个准确生动的说法,数十年来,雷达扫描纷至沓来的新人新作及时而细密,探测此起彼伏的文学潮汐敏锐而快捷。“可以说,仅此两点,雷达在评坛乃至文坛上就有了别人无以替代的一席地位。”
退休后的雷达,仍保持旺盛的工作干劲,甚至比以前更忙了。同时,他也坦承在读书生活中存在不能驾驭的危机,并深深为之苦恼。但是,他仍然怀有坚定的信念:“总得给心灵的阅读留出空间,让读书回到读书的本意上去:不再是精神的桎梏,而在精神原野上的自由驰骋。”不管怎样,他个人的文学批评实践史,又何尝不是中国文学思潮的见证史?他的困惑,又何尝不是时下书界、文坛诸多问题的反映呢?
记者:作为一个当代文学领域的重量级评论家,人们对您的思想的来源、风格的形成很感兴趣。你可否谈一下,在你成长的过程中,谁对您的影响比较大?
雷达:我的母亲对我影响最大。我三岁父亲去世,母亲守寡一生把我抚养成人。上小学前,她逼我每天认三个字,记不住不准吃饭。她是音乐教员,性格忧郁敏感甚至暴躁,但她对古典文学和书法都有很好的感悟力。她对我的影响主要是性格、气质、爱好上的。
我上高中时的青年语文老师,西北师大毕业生,名字叫朱世豪,他不断表扬我的作文,贴到后墙上,还借给我鲁迅选集看。我原先数理化好,结果竟转而报考了文史类。这一改变是决定终生去向的。
我上大学时,一些老师,由北京上海来到甘肃的青年学者对我影响较大,比如胡复旦、徐清辉这样博学的老师。我没有遇上什么“贵人”相助,其实最大的“贵人”就是书本了。
记者:你的第一篇评论是关于哪部作品的?你真正确定走评论的路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还是不自觉地形成的?
雷达:如果单说评论的话,最早是读大学时写过一组杜甫诗歌的阅读札记,投到甘肃广播电台连续播出了,电台编辑以为我是老师。如果要说当代文学评论,应该是1978年初发表在文艺报的关于王蒙的访谈和评述,叫《春光唱彻方无憾——访王蒙》,那时王蒙还在新疆。另一篇是重评《在桥梁工地上》,题目忘了。这也是新时期有关他们的最早的评论,也是我个人最早的有关当代文学的评论。
记者:你对于自己的评论,愿意做怎样的总结?
雷达:对我的评论,我比较认可“理性的激情”这一概括和评价。这是1980年末,刘再复为我的一本书稿写的序言的题目,后来这书没出成。有人指出,我的评论里感性比较丰沛,非常注意捕捉典型形象;感性和直觉并不意味着没有深度,理性的洞察通过感性的方式也可以表述得比较深入。有人认为,我对作品的解读和定位比较准确,能抓住对方的灵魂和要害,从文本、话语出发,不是先验的,不是从概念出发。也有人认为,我对作家作品的阐释常有让作者意想不到的地方,实际上表达的是我自己的审美理想,并不是作品所本有的,很可疑。
记者:你是否也有拿不准、看不透的作品?
雷达:对我来说,确实有许多拿不准、看不透的作品。由于批评资源和知识结构的原因,我与某些新现象猝然遭遇时,甚至出现过失语。任何批评家都不是万能的,都有自己的审美个性和口味偏嗜,都有自己拿手的领域或隔膜的圈子,都有一个寻找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问题。当然,在面对批评对象时,要尽可能准备得充分,调动已有的批评经验,保持对新鲜事物的敏感性,保持批评的良知和公心。
记者:如果让你评价和反思自己,你觉得自己提出过哪些重要观点,你的评论对于当代文学有何贡献?
雷达:对当代文学的研究和评论,学术界的认知度可能比较低;但对从事者本人来说,付出的劳动却往往是艰辛的,要求必须有大量的阅读、活跃的思维以及足够的信息来支撑。由于工作关系,我不得不站在当代文学的前沿,根据自己的阅读和理解,提出过一些看法,至于重要与否,就只能由别人去评说了。但客观的说,有些观点在不同时期发生过一点影响。比如,总结新时期文学的主潮,有人认为主潮是现实主义,或是人道主义,或是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有人则认为无主潮,而我提出了“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是主潮,以为这才是长远性的,不管文学现象多么纷纭庞杂,贯穿的灵魂是这个。再如,1988年3月,在《探究生存本相,展示原色魄力》中提出了“新写实”作为新的审美意识的崛起和它的几个主要特征,那时我管它叫“新现实主义”。
记者:您认为现在文学批评的态势怎样,如何评价,评论的氛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目前评论界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雷达:与过去相比,批评主体、批评资源、批评环境、批评话语、批评类型、批评方式,都发生了大幅度的变化,说起来话就多了。我认为,还是出现了一些优秀的研究成果,出现了一些优秀的青年批评家。但总体说来,文化批评取代或遮盖了文学批评,相当多的文学批评也是以文化研究为指归,比较纯粹的文学批评不断边缘化,空间在缩小,但仍有人在坚守。这与文学在整个文化艺术领域所占份额和影响力的减弱是不可分的。在平稳地发展中,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似乎比以前正常了,而突发式的文学事件比前几年也少了许多,不知是幸还是不幸。从总体来看,文学批评在面对当今的时代思潮、历史语境、现实生活、创作实际时,表现得比较被动、窘迫、乏力,缺乏主体性强大的回应和建构性很强的创意。
记者:在评论界您以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有见地的评论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可是也有个别新潮批评家认为,您是“一个过时了的亚里士多德”。您怎么看?
雷达:我也看到这说法了,也思考过这个问题。我是这样想的,过时不过时,主要看你对新的文学现象,新的作品和新的思潮,能不能作出比较敏锐的、有见地的分析判断,能不能提出新问题,你的表达包括你的语汇是不是新鲜的,为时代所需要,如果提供不出任何新的有意思的东西,观念又很陈旧,语言味同嚼蜡,那就真是过时了。读者的反馈是一种无情的真实,我们必须面对它。我也想努力不懒惰,保持思想的弹性,保持对新事物的兴趣,但这一切只能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尽力而为,是勉强不得的,何况我比较懒。一切随缘吧,能做点什么,就做点什么。(作者:舒晋瑜 原载《中华读书报》)
我的母亲:
甘肃省第一个女法官
雷 达

(年时期的雷达和母亲张玉书的合影。)
10月15日,接到天水王耀先生来信,言他正在编撰《陇上巾帼撷英》一书,想请我写一篇怀念母亲的文章。他说,“你的母亲是一位刺绣高手,某某家中就曾有老人家的刺绣作品悬挂,希望你的文章能以尊母大人的刺绣为主题来写”。我与王先生素不相识,他忽出此言,使我心头一颤,我吃惊于他何以对母亲了解得如此清楚。他说得完全对,母亲青年时代确实以刺绣之精美闻名于陇上,旧社会兰州的《民国日报》还专门发过消息,称为“一绝”。这旧剪报文革前我还见过,贴在一个大本子里。从我懂事起,我家的墙上就挂着一个镜框,内嵌一幅刺绣,在一个“心”字形的图案中央,单绣一个大大的“爱”字,曾挂了很多年。它应是母亲刺绣的代表作了吧。至于它何时消失了,或落入何人之手,我就记不清了。文革前夕我分配到北京工作,只留母亲在兰州,文革一来她受尽了磨难,那幅刺绣可能就此失落在文革的风暴中了。我还听说,母亲的另一幅刺绣,被老家——天水新阳镇王家庄的某人拿去了,家里人去讨要,人家不给,闹得很不愉快。这是文革后期的事。
这些沉重的往事我实在不愿回想。不过,王耀先生的来信使我动心了:我早就想为母亲写一篇文章,不如借此一“催”了却夙愿。我为什么一直写不出在心中默想过多遍的文章,因为它太复杂了太沉郁了,以致每每提笔,临事而惧。这一次我能完成吗?王耀先生索稿甚急,限时很短,准备在11月8日天水妇联建会50周年那天出书,给我的也就十几天,还包括邮寄时间,怎能写得出?看来,只能放下大计划,先写一篇直陈其事的短文了。关于刺绣问题,我没有更多要说的。我要在此披露的是一个连我自己也不清楚的重要史实,那就是:我的母亲张玉书,乃是甘肃省的第一个女法官。
要说清我母亲的事,不能不先简要谈谈我的父亲。我父名雷轰,字子烈,号抱冰,天水新阳镇(沿河城)王家庄人,生年不详,因患肺结核不治,殁于1946年。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农学院,学的是农业经济,在北大创办过《木铎》杂志,文革中我在北大图书馆还查到过。他是1932年北大南下请愿团的学生带头人之一,事发,遭追捕,藏在南京玄武湖一带的草丛中,险些被国民党宪兵的刺刀刺中。我的伯父曾带了一小袋银元,从天水出发,辗转多日,终在南京寻到了他。父亲后来在南京中央研究院短期工作过。我父母结婚的证婚人是邓宝珊将军。邓还介绍我父亲到重庆中训团受训,那时的人主要靠同乡关系。不幸父亲肺病已加重,并开始吐血了,只得中途由重庆返甘。邓宝珊劝说,子烈,你还是先养病去吧。父亲生命的尾声,是在天水新阳镇创办了“天水新阳农校”并任校长,不忘教育救国的梦,在渭河边上度过了他最后一段非常民间化、乡土化的日子。1943我出生于天水县城,新阳农校正是这一年创办的。1944年秋,父病重,只得举家返回兰州治病,直到他病逝,我们一直在兰州。
我的母亲张玉书(又名张瑞瑛、张玉叔)则是兰州人,准确地说是临夏(河州)人,生于1909年初,病逝于1991年底,享年83岁。我只知道,母亲做了一辈子教员,小学教员,中学音乐教员,以敬业而著称,把一生献给了教育事业;我只知道,我三岁父亲去世,母亲一直守寡,忍辱负重地把我和姐姐拉养成人,把一生献给了我们。也曾偶听人说,母亲年轻时受过刺激,心术不正的人欺负孤儿寡母,还暗示坏孩子叫难听的外号,曾使我心如刀绞,欲跟他们拼命。母亲究竟受过何种刺激,在我心中是一个疑问。
母亲去世后,忽一日,宝鸡的陕西第二商贸学校沈克慈先生转来了沈滋兰先生写我母亲的一篇文章的底稿,叫《甘肃省第一个女法官——张瑞瑛》。此文写于1992年元月,距我母亲去世仅二个月。我这才得知母亲一生中的一个重要经历,同时也是甘肃历史上值得记一笔的往事。据这份底稿末尾说明,沈滋兰同期还写有《甘肃省第一个妇女组织——妇女部》《甘肃省第一个妇女问题期刊——<妇女之声>》《甘肃省第一个女邮务练习生——张菊英》等文章,此文是其中之一。它们是否发表过,发表在哪里,我全不知道。作者沈滋兰,女,甘肃著名妇女活动家,与我母亲是结拜姊妹,我叫她沈姨娘。她解放前曾任国民党国大代表,解放后历任兰州女中、兰州七中校长,并多次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下面全文转抄沈滋兰先生的回忆文章《甘肃省第一个女法官——张瑞瑛》:
张瑞瑛(字玉叔),甘肃兰州市人,幼年丧父,家道由富裕迅速没落,寡母在困境中抚养四个儿女,致使她形成多愁善感的性格。她在甘肃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附设初级中学班和师范科毕业,1928年留任附小教员。她擅长音乐,会弹风琴,吹洞箫,练得一笔较规范的墨笔字。
1931年被甘肃省高等法院录为书记官,在此之前甘肃没有任何女性从事司法工作。身为甘肃省第一个女法官的张瑞瑛,得意,兴奋,穿着国民党军服,背扎军官皮带,头戴军帽,颇显神气。对分配给她的工作钻研学习,也能应付裕如。对这一新鲜事物,周围的人们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着。正是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十口所言。她是二十一、二岁的未婚女青年,完全没有应付复杂多样的社会的经验和能力,不友好,不正常的气氛越来越严重地弥漫到她的身边,她感到孤独,手足无措,感到悲愤,终于在极不愉快的情况下,离开了工作了约一年时间的甘肃高等法院。
张瑞瑛离开法院,重新回到小学教师的队伍里,投入地驾轻就熟地做教学工作,安居乐业。后来转到中等学校里教音乐课和其它工作。解放后,张瑞瑛在兰州十四中学曾荣获优秀教师的称号,曾长期任该校教育工会主席。1974年自十四中退休。退休后的张瑞瑛身体健康,情绪高涨,频频往来居住于儿子雷达学(笔者的原名)和女儿雷映霞工作的陕西武功西北农业大学之间,愉快地享受晚年美好充实的生活。1988年她身体渐衰,病渐多。1991年12月16日病殁于女儿家,终年83岁。
沈滋兰 1992、元月
在文中,沈滋兰先生始终称我母亲的原名,并对母亲的情况通过我姐姐知之甚详,可见她们结拜姐妹(母亲大,沈小)的感情之深。在谈到母亲受刺激一节,只是点到为止,并不深谈。这篇文章底稿,姐姐交我后,我一直妥善保存着,但也不想发表。也许是中国人求平安,为贤者隐的心态吧。现在,王耀先生既然如此热心,我就将沈先生原稿和有关情况写出,或许可以补上甘肃妇运历史上的一个小小缺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