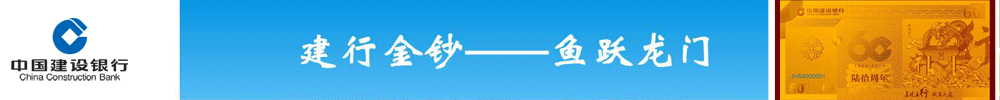 |
○舒垠
跑了一天的风,那时还在跑着,喘息的声音就像一条河流发出的咆哮,而我们则把它叫作风声。风跑进村子后,就有点像玩捉迷藏游戏的孩子。风在这里跑跑,风在那里跑跑。风偶尔也会撞到墙上,发出一声更大的痛叫。都因这夜太黑了,黑夜里行路,确实有些不太好走。风有时也会沿着一条巷子跑,但跑进去后,就发觉有点不对头。它竟然撞进了一条死胡同。风生气了,风掀开那家人的窗子或门,把一家人从梦中惊醒。
村子里,房子像一垒垒扎根地下的石头,房子匍匐着不敢喘一丝气。它怕它即使轻微地喘息一声,也会被这场大风刮走。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房子就不再是房子了,它只能是一只轻飘飘的气球,或者是在大海上没有目标,随波逐流的一叶小舟。
那时候,我正坐在一块石头的腹部,我正坐在一方红漆木桌前,在我的面前,摊开着一本书。我的视线、我的思维被那本书紧紧地牵着。那时候,我也像一叶小舟,在那本叫作《风中的院门》的书里随波逐流,那时,我也像一片树叶,在那本叫做《风中的院门》的书里起落或者飘游。
那时候,屋外的风依旧乱跑着,那时候,屋外突然有人敲门。敲门的声音也像风的声音,“咚咚,咚咚”一声接着一声,挺响,挺沉,那时,我面前的书呈现给我的是一篇《寒风吹彻》的散文。
“咚咚,咚咚咚咚。”敲门的声音更沉了,我怕我再不去开门的话,他一定会敲破我的屋门,会让更大的风涌进我的屋子,把我的房子变成一只轻飘飘的气球,然后卷走。我赶忙走到门前,将门拉开一道细缝。我模模糊糊看见,门口站着一个女人,女人一看见我就迫不及待地喘着气说,“文生拿着根绳走了,你快帮我寻寻。”文生是我的邻居,那个敲门的女人是文生的婆姨。我赶忙将门拉开,文生的婆姨,那个二十五岁的女人,手正按着门板,我看见我开门的时候,她晃了晃身子。
“文生那狗熊和我打架跑了,你快帮我寻寻。”女人又朝我急急地说了一句,就不见了人影。像一股风,她要挨家挨户敲开村里所有人家的门,把村子里所有的人都从梦中叫醒。然后在他们各自的门前丢下那句:“文生拿着根绳子跑了,你快帮我寻寻。”
我赶到文生家里的时候,屋子里早挤满了黑压压一堆人。每个人手里都拿着把明晃晃的手电筒。他们有的站着,有的蹲着,有的坐在门槛上。文生的婆姨站在屋子最中央,嘴一张一合的,表情有些悲恸。那时她正在那堆人中不停地述说着同一句话。“文生那个狗熊,他和我先开始骂,后来就打,他从我大腿上抓了一把,他却拿着根绳子跑了。”女人一边说着,一边挽起了裤管。我看见她肥肥的大腿上果真有一块紫青的伤疤。那时屋外正有人不停地涌进来,进来后就都站着,蹲着,坐着。他们都要听听那女人不停述说着的同一句话,他们都想看看她大腿上的那块伤疤。
“文生那熊跑了,你们快去帮我寻寻。”那堆人仍站着,纹丝不动。“文生跑了,你们快帮我寻寻。”这次是文生女人带着哭腔的声音。文生家屋子里,那时站着黑压压一堆人。
我看见他们仍没有去寻文生的意思,我就站了起来。我说文生婆姨叫咱帮她寻文生哩,咱这么站着,总有些不大对劲。我话音刚落,黑压压的人群开始有了响动,好像他们终于想起了自己要做的事情。黑压压的一堆人开始有了说话的声音、嗡嗡嘤嘤的声音,把屋外的风声也压下去了。黑压压的人终于三五成群走出了门。和我一起的有五个人,我们把寻找目标定在了山上,山上黑压压的一片,我们将手电筒在坡上乱晃,我们不停地叫喊着文生的名字。但我们一直没有听到文生的回声。
“许是真上吊了。”我听见我们五个人中一个人的声音。
“那狗日的熊,害得我们一夜都不能合一下眼缝。”
“那狗日的跑到别人家去串门了也说不定。”
天快转亮的时候,我们五个人回到了文生家里。
文生家里,依旧站着堆人。文生的婆姨,坐在炕沿上,“那熊打伤了我,还自个儿跑了,那狗日的总有这种毛病,他每次和我打架都要跑,但我怎么也猜不透,他这次为啥要拿根绳。”
那时,文生婆姨的声音,潮潮的,不像风。
相关新闻
|